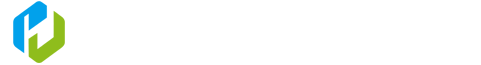



发布时间:2025-09-02 18:12:23 作者:小编 点击量:

当刑事案件进入检察院阶段,案件的走向往往悬而未决。对于大部分刑事案件来说,是否起诉、以何罪名起诉、量刑建议的轻重,甚至案件能否在此阶段直接终结,都会在这个阶段呈现结论。
对当事人而言,这一阶段也是命运转折点。此时,检察院阶段律师介入,往往能够实质性影响案件走向。
尤其是涉及数字藏品、虚拟货币等新型经济犯罪,因案件复杂、争议较大,律师的专业意见更容易成为检察机关评估案件的重要参考。
近年来,因数藏平台“暴雷”引发的诈骗罪、集资诈骗等刑事案件频发。邵诗巍律师团队至今已代理十余起数藏诈骗相关案件,其中近一半最终取得了撤案或不起诉决定。
说实话,这样的比例在同类案件中并不多见,毕竟,在我们办理这类案件的同时,有关数藏平台涉刑案件,在公众视野不断出现的的公开报道是这样的:
也正因如此,每一个案子的办理,我们都承受着不小的压力。但即便在监管高压、舆论聚焦的背景下,我们仍顺利完成了一起又一起辩护工作。
根据实务经验,一旦数藏项目涉刑,绝大多数定罪都会落在诈骗罪或集资诈骗罪这两个高发罪名上。通常涉案金额动辄百万元起步,所以,这类案件,作为辩护律师,必须谨慎选择辩护策略。如果案件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放手一搏,坚定的将无罪辩护推动到底。
因为,一旦诈骗罪名成立,作为数藏平台负责人或主要责任人,当事人可能会面临十年以上刑期。
去年,我接到一起数字藏品平台法人因涉嫌诈骗罪被起诉的案件。抛开案件本身的法律问题之外,对我而言,要说该案和其他我团队办理的数藏刑事案件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可能就是,实际办理这个案件的承办人,是该地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
根据实务经验,当一个刑事案件由副检察长亲自承办案件时,这往往传递出一些信号:
案件重大、复杂或敏感;需要更高层级的协调与决策;体现检察院对案件的高度重视,同时,对承办人的专业能力和经验有着更高的要求等等。
因此,我推断,本案极有可能被检察院内部评估为新型、疑难、复杂案件。这类案件往往需要检察长级别的检察官来“把关”,不仅为了确保案件高质量办理,更因为案件结果可能对整个地区的同类诈骗罪案件处理产生指导意义。
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看,这反而是一个积极信号。它意味着,我所提交的诈骗罪辩护意见,更有机会得到充分重视与采纳。这也让我对接下来的沟通充满期待。
在办理完委托手续后,我第一时间联系检察院调取卷宗,并连续几天仔细研读案卷。随后,我与当事人进行了第一次详细的电话会议沟通,逐条梳理案件内容。
结合在案证据,我的初步判断是:虽然存在部分证据瑕疵,但案件仍有一定希望争取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然而,最终走向仍取决于与检察官的交锋。毕竟,在我看来,现有材料不足以认定当事人构成诈骗罪,但检察院完全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查缺补漏。因此,在检察院阶段保持谨慎,而非盲目自信,是辩护律师的基本态度。
某天,我致电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先就诈骗罪辩护意见进行了初次沟通。从她的语气中,我能明显感受到其干练、果决以及法律人特有的专业气质。她听完我的思路后表示:“这样吧,你把意见整理成书面材料,我来仔细研究研究。”
自此开始,我与检察官展开了长达半年的沟通与博弈。案件先后两次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这段过程更像是一场攻防战:检察官不断寻找可能指向有罪的证据,而我必须以详实的法律论证,去证明当事人并不构成诈骗罪。
与此同时,这又像是一场并肩作战。律师和检察官都在审查公安收集的证据,思考哪些材料可能补充提交,哪些可用于定罪,哪些反而支撑无罪。换句话说,辩护律师与检察官虽立场对立,但在检察院阶段并非绝对冲突。案件能否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最终取决于谁的法律论证更具说服力。
在这一过程里,没有绝对的对错,更多的是法律人之间的专业交锋与相互尊重。(至于本案的详细法律意见,我放在文末,供办理类似案件的律师同行参考。)
这些年来,不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磁场”,还是我个人偏好研究新型、疑难复杂案件,总体而言,我接触到的检察官大多愿意与律师进行深入沟通。
在一些传统类型的刑事案件中(如醉驾、斗殴、“两卡”类犯罪),因为已有统一的处理规则和固定办案意见,检察官往往占据更强势的主导地位,律师的意见难以产生实质影响。
相比之下,在新型刑事案件(如数藏案件、Web3、虚拟货币类案件)中,由于缺乏现成的经验和判例,检察官更需要参考律师的专业分析,也更可能认真倾听并采纳辩护意见。
同时,基层办案人员往往同时处理数十个案件,还要兼顾行政事务,即便想投入更多精力,也常常心有余而力不足。
所以,律师在办理一些新型案件(例如Web3、虚拟货币)或者偏行业属性的案件(例如数字藏品、助贷公司等),在和检察官沟通时,一定要做到充分的换位思考——因为很多检察官可能是第一次接触到该类型的案件,法律是一门应用的学科,只有在理解行业逻辑和商业模式的前提下,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否则,即便办案人员熟悉法条,但如果看不懂涉案行为模式,也容易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误判”。
也正因为如此,律师在提交法律意见的时候,需要尽可能清晰明了的讲清楚几个核心问题:当事人及其所在行业究竟在做什么;该行业的独有特征、行业惯例有哪些;这些行业特征应当如何作出法律评价;以及当事人行为本身应当如何被准确界定等。
清晰拆解行业逻辑,精准定位行为性质,并能够以检察官能够理解和采纳的方式加以呈现——这不仅是具有行业属性的刑事案件有效辩护的关键策略,更是律师专业价值的真正体现。
特别说明:检察院阶段,为充分论证当事人不构成犯罪,本人曾和检察官以口头和书面形式沟通讨论多次。以下内容系对既往沟通要点的整合与提炼,供律师同行在类似案件中参考。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涉及案件的具体细节已作必要删除。
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多用户之所以报案称遭遇平台诈骗,是因为自己买了藏品,结果没人接盘,价格跌了,砸在手里。
我们在代理平台方的过程中,也接到过不少用户的咨询。撇开平台首发价格是否合理、是否具备市场价值不谈,我们观察到,很少有用户是真的出于对藏品本身的喜爱而购买。更多人是抱着投资心理——买首发藏品,等价格上涨后在寄售市场抛售,从中赚取差价。
虽然目前还没有专门针对数字藏品的法律法规,但各地的金融局、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一直反复提醒:数字藏品不得用于炒作、洗钱、代币化、金融化、证券化等挂牌或私下非法交易。并且明确告诫消费者——不要指望通过投资数字藏品实现财富增值,要保持冷静。
在监管文件和司法实践中,数字藏品通常被认定为“网络虚拟商品”或“消费品”,购买者的法律身份是“消费者”,而不是“投资者”。
但现实是,数字藏品基于区块链技术,具有资产属性,很多购买者天然带有投资意图。我们服务的多个平台,即便在购买页面做了显眼的风险提示,依然无法阻止大量用户以投机心理入场。这几乎是行业的普遍现象。
因此,即便平台没有承诺溢价,也没有虚假或夸大宣传,依旧很难避免用户在亏损后选择投诉、起诉,甚至刑事报案来维权。
从用户的报案笔录来看,他们普遍把购买数字藏品当作一种投资行为。购买前,很多人会去了解市场行情、判断潜在价值。也就是说,即便平台在宣传中为了吸引用户有一定夸大,这种影响也没到让用户完全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用户对风险和收益是有预期的,并不是那种“买完才发现被骗”的状态。
数字藏品本身价格波动大,买入后亏损,很可能是市场变化带来的正常投资风险,而不是平台宣传行为造成的。
从平台方角度来看,要认定其构成诈骗,必须有证据证明——在运营过程中,公司实施了哪些具体行为?是仅仅夸大宣传,还是虚假宣传?有没有超量发行、恶意炒高价格等操纵市场的行为?
如果平台没有通过操控价格、虚假交易等手段去制造市场繁荣的假象,交易规则又是公开透明的,用户可以自由交易和提现,那么平台并不符合诈骗罪的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
刑法当中的诈骗罪,不仅需要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还必须在客观上实施了足以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欺骗行为。换句话说,客观行为的查证与认定,是定罪的前提。
经查阅在案证据材料,目前尚无证据显示涉案公司在微信公众号、用户群、宣传海报等对外渠道存在承诺固定回报、保本回购、元宇宙权益等明确收益承诺,也未见虚构合作方(如博物馆、文化协会)或夸大藏品稀缺性的确切证据。
结合公司运营情况,其是否具备区块链备案、艺术品经营许可等资质,以及平台资金流向,均需审查。从目前证据看,公司在实物兑换、权益兑现等方面均有履行行为,未能证明其存在虚假承诺。若承诺内容已得到实际履行,或未对用户形成实质性误导,则难以认定存在欺骗行为。
现阶段证据亦未能证明涉案平台存在通过操控二级市场(如虚假交易、价格干预)制造升值假象的情形,亦无证据表明其利用“空投”“盲盒”等方式诱导用户投入资金后中断服务、限制提现等行为。
综上所述,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涉案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行为。其交易规则相对公开透明,用户具备自由交易和提现的权利。在此情况下,无论是诈骗罪还是集资诈骗罪,在主观故意和客观行为上均缺乏成立的基础。
从在案的员工笔录、微信聊天记录及宣传资料来看,目前尚不足以证明公司管理层有明确的欺诈性策划。相反,材料仅能说明各岗位员工和志愿者在正常履行各自职责,尚无证据表明存在主动炒高产品价值、发布失实信息或刻意诱导用户购买的行为。
目前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平台存在超量发行、未上链发售或利用“老鼠仓”输送利益的情况。更缺乏证据表明相关环节存在主观恶意或具体责任人。
现阶段材料未能显示公司对用户普遍作出“保底回购”“固定分红”等收益性承诺。即便个别宣传语存在夸张成分,亦不能直接推导出诈骗故意。从现有履行情况看,平台对用户的部分权益确有兑现记录,不能认定为整体性虚假承诺。
目前已发行的数字藏品均有相应创作和授权来源佐证,部分还附有签约合同或授权文件。未见证据证明涉案公司在版权、商标等方面存在侵权,亦不足以支撑刑事指控。
从现有财务资料看,公司资产规模、收支情况符合正常商业逻辑。未见抽逃资金、恶意挥霍或异常流向的明确证据。
综上所述,在案证据尚不能证明涉案平台的整体经营模式具有欺骗性或非法性,更不能直接推导出刑事犯罪构成。依照“疑罪从无”的原则,现阶段不宜对平台及相关责任人作出诈骗或其他经济犯罪的评价。
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账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
数字藏品类案件,在判断平台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时,需要结合平台停止运营的原因、事前告知义务的履行情况以及资金处置方式进行综合分析。这类案件当中,用户报案的原因往往描述为:平台无法提现,联系不上客服。
就本案而言,当时数字藏品市场整体处于下行阶段,平台关停属于客观经营风险所致,并非蓄意卷款跑路。更为关键的是,平台在停止运营前已向用户发布公告,并启动退费安排,对用户进行了比例退款。上述行为表明,平台在资金处置上并未表现出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意图,其目的并非骗取用户财产后占为己有,而是受行业整体环境影响被迫退出市场。
首先,报案人所称损失,多数系其在公司平台二级市场购入数字藏品后因未能转售而产生的价值缩水。这部分损失并非直接支付给公司,而是二级市场正常交易过程中的价格波动。公司在此过程中仅按交易额收取少量手续费,因此,不能将报案人二级市场的损失金额直接认定为涉案犯罪金额。
其次,就公司收益而言,平台首发销售收入:约xx万元。公司具备营业执照,该部分属于正常经营活动,依法不应直接计入犯罪金额。平台寄售市场交易提成:约xx万元。这部分同样属平台合法收入。
综上,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公司收益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取得,且所谓“损失金额”并未直接流入公司账户的情况下,将报案人全部损失数额等同认定为犯罪金额,既缺乏事实基础,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我们团队自数字藏品行业兴起至今,已为数百家平台提供服务,与行业用户有过广泛接触,因此对该行业的用户特征有较为深入的理解。
与传统理财公司暴雷案件的被害人群体不同,数字藏品用户的整体画像、交易动机和风险认知存在明显差异。
以我代理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为例,这类案件中,被害人往往是在公司长期高收益宣传诱导下,将养老钱、全部积蓄投入其中,一旦公司暴雷,个人与家庭财务彻底崩溃。
而在数字藏品领域,用户大多基于投机心理参与交易。他们普遍活跃于多个平台,通过低买高卖、炒作热点来获取差价收益,极少数用户是因真实的收藏兴趣而购买。购买后的主要意图是择机在二级市场抛售,而非长期持有或纯粹收藏。
因此,一旦出现亏损,这类用户往往会组团报案维权。更有甚者,一些用户长期在各平台流动交易,深知此类行为具有投资风险,但仍愿意投入资金“试水”,心理预期是“先投入一部分,赚到钱就离场”,其本质上带有明显的赌博心理
本案系被害人xx报案致案发。辩护人能够理解,公安机关出于“维稳”的心态,对平台予以立案调查,且客观来讲,在立案之初,由于数藏属于新兴行业,本案的立案有一定程度上的原因是由于公安机关对平台经营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认识性不足。这也是案件进入刑事程序的原因之一。
从经营模式看,本案平台的盈利主要来源于首发销售及寄售市场交易手续费,符合当时行业普遍规则,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数字藏品作为特定作品、艺术品的唯一数字凭证,经区块链技术赋能,具备唯一性、不可篡改、不可复制等特征,本身具有一定收藏与欣赏价值。用户在寄售市场的售出价格由市场供需决定,与平台无直接关系,平台仅提供交易场所与技术支持,并不参与价格制定。
他们并非基于单纯的收藏喜好购入藏品,而是在多个平台间流动交易,秉持“只能赚钱,不能亏钱”的投机心态。一旦出现亏损,便通过集中报案寻求所谓“维权”。在本案中,这种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当时司法机关对数字藏品行业认知不足、法律规定尚不明确的背景。
因此,对此类报案行为在性质认定上,应谨慎评估其是否真正符合刑法保护的“被害人”范畴,并应当防止将正常投资风险转嫁为刑事责任,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不当占用。
在大量传统的帮信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电信诈骗案件中,公安机关在制作被害人询问笔录时,通常会使用较为固定的问答模板,重点围绕反诈宣传、反诈App安装、是否接到劝阻、转账时间与金额等问题展开。这类模板化的询问方式,在电信诈骗案件中或许可行,但并不适用于数字藏品领域的涉刑案件。
报案人称“看到涉案平台宣传活动,了解到平台属于利润投资,就往平台里充钱”,
公安机关随后直接询问“是否收到过反诈宣传”“是否安装过反诈App”“是否有民警对你预警劝阻”等问题。
上述问答模式显然是沿用传统电诈案件的模板,与数字藏品平台的实际运营模式、用户交易逻辑并不相符。辩护人有理由怀疑,这些笔录并非完全反映报案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接报民警基于自身理解和固有模式所作记录。
此外,在案银行流水与至少3名报案人的笔录内容存在出入——其陈述的充值、提现金额与实际交易记录并不一致。倘若本案最终拟按诈骗罪定性,则有必要逐一联系各报案人,进一步核实:
只有在上述关键事实查清后,才能依法判断平台行为与用户损失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在此类案件中,司法机关通常会就争议事实对平台负责人、股东、员工进行询问,并通过交叉验证予以确认。例如,关于是否存在超量发行、未上链发售、“老鼠仓”等行为,完全可以通过技术后台数据进行查证,而不仅仅依赖员工口供。
本案中,部分员工的证言对当事人的指控,我们认为其真实性、客观性不足,理由如下:
相关员工仅为证人身份,而非案件从犯,不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其口供缺乏自我风险约束;
由于公司后期经营不善,确有拖欠工资情况,部分员工对公司法人存在情绪和怨言,在作证时声称平台存在“老鼠仓”等行为,其陈述难以完全排除主观偏见;
目前未见有其他直接证据能够印证该类证言,尚不足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本案当中,员工证言必须结合案件全貌和其他客观证据一并审视,不能单独作为定案依据。在缺乏技术数据或其他客观证据印证的情况下,不应当将员工的不利陈述直接采信。
综上,辩护人认为,经两次退侦,认定xx构成诈骗罪仍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恳请检察院对其做出不起诉决定。
本文为邵诗巍律师的原创文章,仅代表本文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对特定事项的法律咨询和法律意见。文章转载、法律咨询、同行交流,请添加:sswls66。
家属必看 刑事案件律师会见,我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以一起买卖虚拟货币涉嫌非法经营罪案件为例
《经济观察报》专访邵诗巍律师:DeFi、稳定币挖矿等虚拟资产投资为何刑事风险频现?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88号

电话:400-123-4567

点击图标在线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